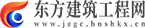【环球播资讯】唐小雁与徐童的“俗世”全宇宙
一镜到底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“百年好合,百年好合!”
春风吹到北京城,又刮来了潮白河东的河北燕郊。自打年初公布与导演徐童的婚讯之后,唐小雁就源源不断收到祝福——带着几分“传奇”,以及如今世上难得的情义,这对江湖儿女的故事在网上传出数个版本。唐小雁觉得这样清一色的祝福实属罕见,也感动于“感觉好多人比我自己还激动”。
这已经是燕郊今年春天的第三场沙尘暴了,但无论外边儿的风怎么刮,小区的屋里倒是清净,四十多种植物被唐小雁养得绿油油——像是南方才生养得出的植物,一旁的加湿器还在继续喷水雾。初来拜访的人容易被家里的纷繁物件晃了眼睛,随处可见的草莓熊玩偶、纪录片剧照、超级英雄手办、书籍,却呈现出奇妙的和谐。风在窗外旋出口哨声,屋里响着电子蝈蝈叫。
“再出去摸爬滚打,折腾得一身受伤了,也不怕,你有个地方休息。”50岁的唐小雁在家收拾着刚到的绿植,她自小爱热闹,穿着桃红色卫衣,扎着高马尾,红唇,两道细眉似柳梢般飞扬,细钻鼻钉亮晶晶。
58岁的徐童在一旁补充,整个家的设计和摆设全靠小雁,有时他也叫她老唐。徐童脑袋剔得溜光,自认“外热内冷”,说话时神采飞扬,安静时看起来不想搭理世上任何人。
从2009年徐童在燕郊拍摄纪录片《算命》起,两人的生活开始交织。那时唐小雁做着处于灰色地带的按摩房生意,《算命》的镜头闯入她的生活后,她继续在徐童纪录片《老唐头》里出镜,接着担任徐童纪录片的制片和摄影,走向了另一种工作和生活。两人也渐渐相恋、结婚。这些年里,他们因纪录片而不断投身他人生活,展开“生活实践”,纪录片早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2023年4月初,北京电影学院,近日上映的高口碑伪纪录片形式的剧情片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放映结束后,影片导演孔大山说到徐童的《算命》对他的影响,尤其谈到片中令他印象深刻的唐小雁女士,“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角色,特别有情有义。”以至于他在写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中的女性角色秦彩蓉时,“就把她脑补成唐小雁女士的性格特质,特别的心直口快,但是又特别的重情重义。”
台下观众席,唐小雁举着手机拍摄着台上的孔大山,随时记录早已是她的生活习惯。镜头接着转向邻座。受邀发言的徐童,徐童围绕着影片与纪录片形式、道德与真伪畅谈了数分钟。当电影主创们邀请唐小雁分享时,徐童自然地接过了唐小雁手中的手机,继续拍着这个长镜头,递去话筒时娴熟地调动气氛:“怎么没找你演呢?”
“如果直接找我演,我演得比她还好。”接过话筒的唐小雁照样心直口快,现场反应热烈,几阵掌声欢笑。
▲唐小雁在 《老唐头》 拍摄现场 图/受访者提供
对纪录片观众来说,唐小雁并不陌生。作为徐童多部纪录片中的人物,唐小雁带观众进入了一个在主流社会中被遮蔽的游民世界,并展现着这个世界的另一套运行规则。“游民系列”至今仍是徐童的纪录片代表作,他的镜头对准城市边缘的性工作者、小偷、算命先生、流浪艺人、孤独老人。徐童执着于呈现人在极端困苦生活中的生命力。他拍摄的游民世界正是唐小雁置身的世界,而徐童的拍摄和剪辑也令唐小雁这股强韧的生命力得以绽放。
2011年,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开幕式上,唐小雁获得首个“真实人物奖”,授奖词指出,“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,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。”尽管是否该颁奖给纪录片的真实人物至今有争议,但唐小雁的获奖感言倒是实在的大白话——
“我觉得这奖就该我拿,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帮人,你们这些导演就喝西北风去吧!”她说。
最初,观众为唐小雁在《算命》等纪录片中袒露的生活而为她提心吊胆。在镜头外,徐童的朋友们也为他捏了把汗。2010年,纪录片导演、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黎小锋与徐童有过一场对谈,“面对八字先生、乞丐、智障和有的底层人士,摄像机稍不留神就构成了对他们的窥视甚至侵犯,你怎样把握自己的道德底线?”黎小锋也担心徐童接下来要怎么走,“我们在看的时候,心里都有些牵扯。感觉你已经完全进去了——”
“拍这类故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,从一开始我就十分渴望过另一种生活。我希望感同身受。”刚开始拍纪录片两年的徐童说,“我希望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,开始一段‘负罪感’的宿命般的表达。”
▲徐童在 《老唐头》 拍摄现场 图/受访者提供
接着十多年,徐童继续投身纪录片,探索这一形式的边界。他的最新纪录片关于东北养老院,片中大量使用了GoPro拍摄,主视角代入感非常强。拍摄期间,唐小雁和徐童在黑龙江这家养老院住了一年,并承担了院里的护工工作。2022年6月,徐童拍摄完成他的第一部剧情片《三个十年》。唐小雁的镜头对准了拍电影时的徐童,这一次,徐童成了唐小雁的纪录片中人。
“至少在国内的纪录片导演中,我觉得我们是把生活和拍摄现实最模糊化的,给它合二为一。”徐童说。
鲜血淋漓似桃花
最初去黑龙江养老院的原因很简单,是因为老唐头不断的电话召唤。
入住养老院后,纪录片《老唐头》的主要人物、唐小雁的父亲唐希信原本特别高兴,然而不久后,老唐头心仪的老太太不搭理他了,九十多岁的老唐头感到被孤立,于是常常在养老院院长身旁,故意拉高嗓门给唐小雁打电话,“凤儿(唐小雁小名),这儿虐待老人啦,你和徐童赶紧过来曝光这养老院……”
“院长你往死里收拾他,他就这么能作。”唐小雁接电话时大笑。
2018年6月,唐小雁和徐童回黑龙江去养老院看望老唐头,也顺便探探路,看养老院里有没有得拍。这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养老院远比他们想的热闹,老人之间有处对象的、打架的、掰扯的,不少人都和老唐头一样生命力旺盛。到养老院的第一周,她和徐童心里就有了数,“有得拍。”他们与养老院院长和老人及家属们谈妥拍摄,再回北京参加侄女的婚礼,接着在燕郊家里准备了一车摄影器材和行李,开着四驱大车跟搬家似的往东北去。
离家前,他们就商量好了,拍摄养老院的纪录片,要在养老院住满一年。同吃同住是他们从第一部合作纪录片《挖眼睛》以来默认的拍摄原则。他们和入住的老人一样交养老费,一个床位每月1000元,管吃管住。
养老院有二十多位老人,两层楼,唐小雁和徐童住在楼上,他们每天都在拍素材。但空闲时间那么多,唐小雁总忍不住帮忙干活,她热心肠,也手脚麻利,帮忙收拾屋子,“楼上那个厕所归我管。”她觉得徐童干的活更多,“他是护工,给老人擦屎擦尿,每天倒尿盆子,乱七八糟的他啥都干。”一位卧床的老人一直喊徐童“六弟”,让他帮忙喂白酒。有时老头们打起来,他们还得劝架。
在养老院,唐小雁和徐童既是入住者,又是护工,还是老唐头家人,一起经历着老人们在晚年群居生活里的日常,还有那些啼笑皆非与荒诞,“我们从来不是把记录放在最前面,只是为了拍片子去的。这些丰富的身份层次能够像我们的触角一样,在这里扎得特别深。同时我们有很强的角色感,能够关注到养老院老人们的吃喝拉撒和生老病死,一切都是体验式的行为。”徐童说。
这部关于养老院的纪录片《他们是肉做的&肉是怎么做的》有七个多小时,依然是强烈的徐童风格,鲜活、淋漓尽致。相比徐童以往的纪录片作品,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觉得受到了冲击,“一是视觉上的,他是用主观视角,各种GoPro拍的;二是他自己直接参与其中,比如会介入老人们的事情;三是尺度很大,拍到老年人偷情、争风吃醋。”对徐童和唐小雁这样全身心沉浸的拍摄方式,“觉得挺震撼的,就是他们这把年纪了,还这么费心力,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很惭愧。”
似乎在任何拍摄环境里,徐童都执着于关注人的生命力,而在纪录片中呈现出一股活泼和动势的鲜活气息。影评人王小鲁曾评价徐童在纪录片中呈现苦难的方式为“鲜血淋漓似桃花”。“我们做义工一起经历他们生命的末端,但这个终点站不是悲切的,而是生命的狂欢。当然其中也有特别悲苦的,最后瘦成一把骨头,衰竭到油尽灯枯。”徐童说。养老院里,他们也经历了几位老人的死亡,他当护工帮忙照护老人的遗体。
在养老院待一年,对唐小雁来说有另一重意义。自15岁离家后,她和父亲老唐头就没有这么长时间相处过了,“我在养老院待着,老头非常高兴非常踏实,其实他就想让我在那陪着他,但谁家姑娘没事在养老院陪他爸住,那是因为工作的原因,就陪老父亲待了一年多的时间,要不然还真没有这个机会。”
“2008年我妈没了,2009年我回去家里没妈了,就一个老头在家。我的天,那老头才有意思,和谁都能处,会模仿好多小鸟。”唐小雁说。2009年秋天,纪录片《算命》之后,她回黑龙江老家想做黑窑生意,邀请徐童来玩。徐童见到了唐小雁的父亲老唐头,老唐头的语言能力极强,见到纪录片导演来家里特别高兴,在镜头前尽兴施展,唐小雁的三哥也爱说爱聊,“碰着家里来了一个拍纪录片的,都特别愿意给人分享。”她说,这便是纪录片《老唐头》的由来。
▲2010年,唐小雁回东北老家,帮外甥女家上山放牛。图/受访者提供
自《算命》《老唐头》后,徐童以唐小雁的四表哥和三哥为拍摄对象拍下了纪录片《四哥》和《两把铁锹》,再加上《他们是肉做的&肉是怎么做的》,多米诺骨牌式的人物关系组成了一组东北家庭的纪录片影像史。这是宏大叙事之外,以非常个人的方式记录了普通个体的悲欢人生。
在电影节和放映活动上,唐小雁在不同人生阶段反复观看这些纪录片。
《算命》刚出时,她作为拍摄人物受邀参加放映会,那时她离片中的生活还很近,跟着大伙儿一块儿看,没什么感觉,“因为那就是我的生活,就是我自己。”
又过了五六年,唐小雁在深圳的一场放映活动再看《算命》,她嚎啕大哭,直到最后整个人都失控。那时她已经从原来的漂泊生活走了出来,“再看才知道,我那个时候经历了这么多,原来这是我的生活。”于是她不再看《算命》。
算命与改命
2008年,河北燕郊,34岁的唐小雁到算命先生厉百程那儿时,没搭理正在屋里拍纪录片的徐童,她的重点在算命,“毕竟给了钱,在特别认真听算命的怎么说。”
“你就是孤单命了。”厉百程建议她改名。
她就此改了名。那时,她在燕郊开了两年按摩房,正遇到无赖的纠缠。15岁离家后,她一直在为生计四处奔波,干过很多工作,被坑过钱、也被性侵过。30岁时离了婚,有一个孩子,尽管生活充满不安定,但她始终每个月给东北老家汇钱。“一个女的,没人帮你,打掉牙得往肚子里咽。”那时她常去算命,身边没人可商量,算命对她来说是开解,一次10块钱,一次能讲半小时。
后来,徐童来她店里拍摄时,唐小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,她自己也有DV,爱拍照、拍视频。哪怕徐童的镜头凑到跟前了,她也懒得管。《算命》记下了唐小雁那时的生活状态:她用不在意的语气说起22岁被性侵,“我还得哄着,必须得回去啊”;她和店里认的干女儿痛哭,“我很孤独,没有人保护我”;她抡起棍子棒打纠缠她的无赖,再甩两百块钱给他缝针;她在夜里痛哭自己的生活,拿针刺破肚皮穿转运绳,第二天照样扎起高马尾、描眉、涂口红。
▲河北燕郊,纪录片《算命》拍摄期间,唐小雁躺在自己的床上。图/受访者提供
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,唐小雁进了看守所,那时远在云南参加电影节的徐童赶回北京,把车抵押了将她赎了出来。唐小雁为报恩,同意把她的镜头放入《算命》里,接着帮助徐童拍了《四哥》《老唐头》等片子。她游刃有余地帮徐童处理着拍摄关系,徐童想拍摄的游民世界正是唐小雁置身的世界,而那套处世规则是她在生活的摸爬滚打中习得的。15岁离家后,她跟着一群小混混学着怎么保护自己,“故意骂骂咧咧,把自己伪装成流氓,别人才不敢惹你,不能柔柔弱弱的。”
最初几年,唐小雁受邀参加这几部纪录片的放映会时,有些观众害怕她——觉得她是危险的江湖中人,也有一些观众觉得她酷,在提问时展现出对她的生活的强烈向往,想跟着她体验生活。
“千万别,我的生活你们看着就行了。”她每一次都诚恳地细细劝解,她在成长中得到的学习机会并不多,只读到小学,便不得不做工赚钱,“像你们现在的生活多好啊,又能学到知识,又能上大学,又能有好的工作,这多好,你们真应该享受现在的生活。”
2013年,编剧芦苇向徐童推荐了一位唱二人台的民间艺人“二后生”,他在内蒙古草原流浪演出,双目失明。徐童觉得这是很好的拍摄人物,但预感这样的江湖艺人应该接触难度挺大,有了前几部纪录片的铺垫,他邀请唐小雁一起参与这次拍摄,虽然也不知道片子最后能不能拍成。但就像以往遇到任何生机一样,唐小雁非常珍惜拍摄机会,途中,几个箱子都是她扛,奔波一天后凌晨雪天开车她也撑住精神,她永远神采奕奕、乐观,办事牢靠。但二后生对他们的态度反复不定,今天让跟拍,明天又不认了。
一问才知道,二后生误以为她和徐童要拍他们演出刻成碟片卖钱。唐小雁拉着徐童和他们好好解释,她知道怎么和他们打交道,首先掏家底一般地介绍自己家里几口人、各是做什么的,再找演出团里最好接近的人唠嗑,送二后生的老婆新衣服。另外,二后生让唐小雁跟他一块儿演,她也大大方方上台临时客串个小角色。最重要的是,她依然有股本能的善良,当二后生和盲眼母亲又要分别、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时,唐小雁抱着初次见面的老太太开始哭起来,为这对母子分离而伤心。
她在拍摄中慢慢了解纪录片。拍摄在冬天,住宿的旅馆有正常房间,但徐童选择和二后生的演出团一起挤在15块钱一晚的大通铺,枕头和褥子上长了黑毛。唐小雁一直有洁癖,去别人家超过两个小时,就忍不住给人家马桶清理干净,但她在拍摄中也全程同吃同住地参与。“你要跟他们同吃同住,证明你跟他们是一样的,这样人家才能接纳你。”零下三十多度的天,二后生还在室外的台子上唱着二人台,她望着二后生,感受到一种生命的痛苦和能量。
“你跟不同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,会体验到他们的生活。刚开始心里觉得又苦又累,再一点点地觉得非常有意义。”她说。
在二后生的纪录片《挖眼睛》中,唐小雁第一次担任了制片人,这意味着另一个世界向她打开了一扇小门。她很珍惜参与纪录片的机会,也前所未有地渴望曾经缺失的学习,她大量看电影,一点一点从头学电影相关的知识,也学习如何摄像。从《老唐头》开始,她在徐童纪录片中的参与越来越深,已经担任了数部纪录片的制作人,还在《赤脚医生》和养老院的纪录片中担任摄像之一,至今依然在研究如何解决镜头虚焦的问题。
尽管这些纪录片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进行放映,但唐小雁觉得拍纪录片的生活非常踏实,“即便没有钱,即便什么都没有,但给后人留下了特别多的东西。将来有一天你没了,人家会看到你留下的这些东西,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会看到的,对不对?”她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记录。
做纪录片10年后,唐小雁终于拥有了独立拍摄纪录片的机会,这也源于她一直以来的视频记录习惯。
2022年3月,徐童的第一部剧情片《三个十年》在陕西汉中开机,这部电影由芦苇编剧,阿城担任艺术指导,改编自徐童的小说《珍宝岛》。在正式开机前,唐小雁早已记录下此前的剧本讨论、剧组筹备的过程。她和徐童有了将电影拍摄过程拍成纪录片的念头,影片的投资方也有这样的想法。最终唐小雁成为这部电影幕后纪录片的导演,又找了两位助手一起合作。
这部电影是年代戏,涉及到对上世纪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的还原,拍摄工程量挺大,徐童没有参与纪录片的工作,但对唐小雁的拍摄很好奇。“小雁经过这十多年,从我的拍摄人物,到跟我一起拍纪录片,变成我电影制作的拍摄者。在镜头内外,她自己完成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”
▲陕西汉中,唐小雁与徐童在电影 《三个十年》 的拍摄现场 图/受访者提供
一百多天的拍摄中,唐小雁成了剧组里最早起最晚睡的人。徐童拍电影,她拍徐童在内的电影相关的所有事儿,拍剧组里的人们,拍片场围观的居民。“简直疯了,一天到晚开心得不得了。这个片子我担任导演,我就特别兴奋,永远都不累,在现场永远都使不完那劲儿。”因为担心错过什么,唐小雁拿着机器一天站十多个小时,敏锐地盯着现场,一有情况马上跑过去,完全不知疲倦。
徐童觉得,唐小雁身上始终有一股韧劲儿和乐观,遇到喜欢的事时有孩子一样的天真和投入,游走在任何环境中都有着本真的善良。在剧组,除了拍纪录片、拍剧照,唐小雁经常给工作人员拍工作照——没有任何人要求她这样做,她甚至给每个人建好文件夹分好照片,问来邮箱,挨个发过去,“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要给家人看。我知道出门在外工作都很不容易,也会想给家里人发点自己工作的照片。反正我对人就是诚心诚意地交。”
她始终像石缝里的种子,奋力地汲取周围的光和露。在两百多人的剧组中,“拍片子拍东西,但你永远都在学习。”独立拍片也像对以往拍纪录片工作的检验,唐小雁有时在现场拍着就特别兴奋,“因为你都知道怎么剪,连素材框架都有了。”怎么拍怎么走位,她心里都有数,“有信心,就上瘾了。”
珍宝岛上
2007年冬天,北京宋庄,40岁出头的徐童开始写小说《珍宝岛》,那是他和游民社会的最初交锋。因写作,他流转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,整个游民世界对他都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,放逐、鲜活、危险,这里有另一套生活法则。
在那之前,徐童一直沿着主流社会的成功道路一路朝前。1965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徐真是新中国第一代科教片编剧、导演。1980年代他在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学新闻摄影,尽管毕业后没能进入体制内工作,但也乘着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风一路向前,他拍过电视剧,进过广告公司,做生意小赚过,也血本无归过,起起伏伏。
“当时我觉得已经过了很长的人生了,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,从上学到下海做买卖挣钱到蹚当代艺术的浑水。我的前40年好像是给社会交学费,但实际都是在弯弯曲曲地寻找,敲各个门,只是都打不开。”徐童说。
40岁出头,徐童忽然开始写小说,在人生的低谷。他想把自己经历过的时代狂飙和理想幻灭记录下来,看时代在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那个冬天,他在北京宋庄朋友的工作室里安心写作。在这之前的生活,他都热切地投身时代洪流,获得成功与失败。记忆中那个冬天有很多场大雪,屋里冷,空得说话都有回音,窗外大雪簌簌打落在地,他在本子上写着《珍宝岛》的故事,梳理以往内心所掩埋的,觉得什么东西开始变了。
那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,“倒不是悲观,心里有一种沉寂感,轰轰烈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。”他觉得自己成了外热内冷的人,对生活和生命的感受也变了,那时他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里,一切都是瞬间,太短暂,“在这么一个宏大尺度上,突然就觉得放松了。没必要那么争,也不值得再在这么一个短暂瞬间里,非得还要去怎么样。”
徐童几乎把人生像从头翻篇一样重新审视,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,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?
不再继续主流认可的道路,在四十多岁开始拍纪录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哪怕在以往,徐童也隐隐感觉到有一种其他的生活在召唤,无论是从小的好奇心,还是父母在纪录片和文学方面给的启蒙,改变生活的心一直跃跃欲试,消灭不掉。“只要是温度、养分,阳光、气候到了,一有机会就要冒出来。”他携一台小摄像机走进周围的游民社会。2008年,43岁的徐童拍摄了自己的首部纪录片,关于京郊性工作者的《麦收》。那是一部文学性极强的作品,也是一部引起相当大的关于纪录片道德伦理讨论的作品。
当他开始拍摄纪录片时,就期待一种拍摄方式,“我是指一种游刃有余的,就是一种自由的境界。它能让我把遗憾降到最低。一段戏把它拍得鲜活,拍得淋漓尽致。”2010年,他觉得相比于生活,纪录片反而是副产品,“我的片子就是我的一段生活实践,一段生活史。”
▲2008年,拍摄 《麦收》 的徐童 图/受访者提供
在燕郊拍《算命》时,他遇到了唐小雁,这是后来片子里一条耀眼的支线,也与他自己的人生相逢。但他在拍摄过程中,更多时候是跟着算命先生厉百程,厉百程和老婆石珍珠待他亲近,俩人争执时,厉百程还向镜头后的他求助,“徐童你和她说说。”徐童融入得很好,直到跟着厉百程回老家,看到深冬街头睡在棉絮被里的乞丐,他问出了当时的自己和厉百程最本质的区别:活着这么辛苦,这么没有乐趣,干嘛还活着呢?——生命的虚无,生活的意义,这些问题依然不时困扰着他。
“没乐趣就不活了么?你这话,太无情。”厉百程的答案是生命本身。
十多年的纪录片拍摄中,徐童也以强烈的个人风格,回答着自己当初的提问。“徐童不是在拍社会各阶层的调查报告,他是在拍摄生命力,他借用被拍摄对象的元气,又通过情绪性很强的音乐、鼓动性拍摄手法、剪辑或观念蒙太奇,来强化生命力这个东西。”王小鲁曾写,徐童的纪录片作品实际上张扬的是一种生命态度。
在王小鲁看来,徐童拍的作品介乎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,“这种做法本身就容易导致伦理问题,他与被拍摄对象唐小雁也建立了令人惊艳的关系,关于中国纪录片伦理的最强烈的觉醒和讨论,几乎都是从徐童开始的。但我称徐童和唐小雁是勇敢的创作者和生活者。”
▲唐小雁与徐童在河北燕郊家中 图/本刊记者 姜晓明
每当结束了长时间的拍摄,回到燕郊的家,唐小雁就感到无比放松和舒心。虽然目前这种随时要风里来雨里去拍片子的日子谈不上稳定,但比起最早孤身跑生活,现在的她很安心,她收获了事业和创作,收获了尊重和喜爱,人们喊她小雁姐,或唐女士。尽管她和徐童依然会去探望厉百程和石珍珠,但她不用再去找算命先生开解,身边有人一起面对生活。不断有人问她厉百程的联系方式,说自己也想算命、改命。
徐童觉得,他们现在的状态依然是半个游民。最初的《珍宝岛》被改编成了电影,电影由自己来拍,又由小雁来拍他的电影纪录片。“好像活成了一个传奇故事了,变成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一起活着。”他们穿梭于他人的生活,又回到家中,“就像回到岛屿之间的平静水面,一对饮食男女,带着纪录片去建立很多岛屿。每一个岛屿都是从庸常水面上创造的不同生活,这样的人生连缀在一起,在宇宙永恒的离散中,提醒我们瞬间的意义。”他说。
标签: